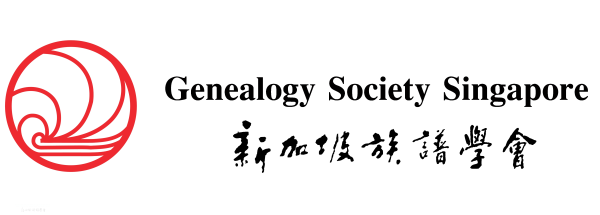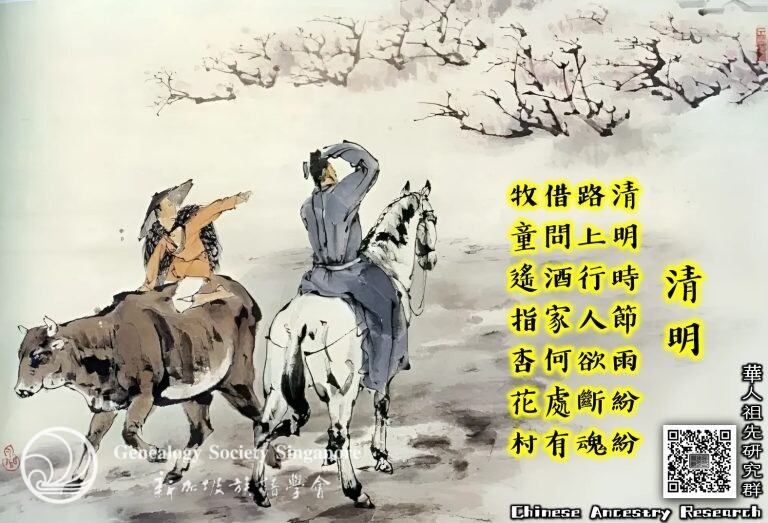
为什么我们要记得
在中国文化中,有一种美德就像家屋的栋梁,撑起了整个家庭——那就是孝。
它是我们把最后一个饺子留给奶奶的原因,是我们不打断长辈讲故事的原因,也是我们接到父母电话时,总会有点紧张地说一句“我没事呢,我在吃饭呢!”的原因。
但“孝”不止是对父母的尊敬,它是一条逆流而上的情感之河,奔向那些比父母更久远的先人——哪怕他们早已离世。对中国人来说,敬祖并不是一种充满阴森气氛的仪式,而是延续,是认祖归宗,是知来处明去处。
西方文化中有诸如“万圣节”或“诸灵节”的纪念日。而我们有清明节——一个不仅用来哀悼,更用来记住、团聚的节日。有时我们甚至会在祖坟边烤整只乳猪,孩子们在杂草丛中追逐打闹,热闹非凡。
清明节总是在每年四月初,一般落在4月4日至4月6日之间。今年是2025年4月4日,正值周五——春意融融、清明如洗的好时节。天是亮的,树是绿的,风里带着新生的气息。中国人选这一天来祭祖,绝非偶然——这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之一,用最好的日子献给先人,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孝意。
“清明”这个词的本意就是“清澈明亮”。它既是扫墓清尘的日子,也是清理心中记忆尘埃的时刻。扫的不只是坟,更是家族记忆;擦亮的不只是碑,更是血脉相连的故事。你甚至可以趁此机会,给孩子讲讲他们的姓氏,不只是一个称呼,而是一段穿越数百年历史的线索。
“清明”原是古代农历中的一个节气,但真正赋予它神圣意义的,不是天象,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归。回到那座熟悉的山岗,走上祖辈走过的小路,回到那块刻着太爷爷名字的墓碑前——这份执着的归途,才让清明节成为中华民族血脉的纽带。
清明节的早期根源
清明节的早期根源
早在 清明节 成为一个象征祭祖、烤乳猪、点红烛、拿竹耙的节日之前,它的雏形只是中国古历中的一个节气标志。
早在周朝(约公元前1046年—前256年),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仰望星空,勘定节律。其中有一个节气名为“清明”,空气变得澄澈,阳光变得明亮,万物开始生长。
但周人不只是天文历法的制定者,更是礼制的维护者。《周礼》一书中记载了“冢人”和“墓大夫”等职官,专司国家层面的墓地与祖先祭祀。这些人不仅是守墓人,更是记忆的守护者,负责确保祖先得到应有的祭奠,不被后人遗忘。
到了战国时期(公元前475年—前221年),连平民百姓也开始在清明时节前往家族祖坟,带上饭菜美酒,肃立跪拜。这种祭祀不再是帝王专属,而变成了全民心中的道义——哪怕祖先早已作古,也依旧值得被缅怀。
但此时,“清明节”这个节日本身还未正式形成。祭祖归祭祖,节气归节气,二者尚未合而为一。
直到唐朝(公元618年—907年),文人荟萃、礼乐隆盛,清明与扫墓才逐渐紧密相连。唐代统治者大力提倡以清明节行孝道、崇儒教,清明的仪式慢慢吸收了更早的春日习俗,如寒食节、上巳节。寒食节本为禁火食冷之日,上巳节则是踏青、洗涤厄运的日子。随着时间的流转,放风筝、吃冷食、春游、祭祖等活动逐渐融合,清明节也从一个节气演变为春日祭祖的节日。
如今若你去问那些来自中国南方的家庭,他们未必会谈起哪个朝代。但他们一定记得那条通往祖坟的小路,记得香灰的味道,记得纸钱在火中卷曲燃尽的样子,还有长辈的一句话:“跪下,这就是你从哪来的。”
上山,也是归根
上山,也是归根
在中国南方,清明不仅是一段时间,更是一种气息:青草味混着烧纸的烟气,远处有公鸡打鸣,大姨又在骂堂弟没带香。 这里没有肃穆的静默,只有热闹的、生生不息的人间。
在广东,这种祭祖活动叫“扫山”或“拜山”;在福建,有人叫它“挂墓”;在客家山区,干脆就说“上山”。不论叫法如何,场景大同小异:一家老小拎着烤肉、水果、叠好的金元宝纸钱,甚至还有一壶热茶。孩子们带着扫帚,总有人忘带打火机。
杂草被除去,新土填上,香点起来,供品一一摆放。有人讲话,有人笑,甚至有人开始野餐——这不是亵渎,而是团圆。活人和逝者,在这一刻重新相聚。
在海南、台湾等地,风俗略有不同。有人用整只鸡或糯米糕祭祖,有人烧纸别墅和“纸iPhone”,寄往阴间。在台湾,清明节是国家法定假期,许多家庭会专程横跨全岛,只为回乡祭拜一座祖坟。尽管形式各异,核心却始终一致:清墓,献礼,认祖归宗。
当然,还有很多人,已无法“回山”——因为那座山,早已在异国他乡。清明节的精神,早已随着华人移民的脚步漂洋过海,从马尼拉到蒙特利尔,在新的土地上扎下了根。
有些人在家设立祖先牌位,摆上照片与水果;有些人去本地公墓,祭拜那些在异乡扎根的近代先人。在东南亚,一些华人社团还会组织集体扫墓,为那些亲属散落他方、无暇归根的家庭代为祭拜。
有时,清明是一家三代围着视频电话,看着潮州老家堂哥代全家焚香。有时,它只是厨房角落里,一人一柱香,对着一张旧照,说出一句只有先人听得到的感谢。
无论身在何处,无论形式如何,清明节的意义从未改变: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哀悼,而是一次对生命的确认——我们仍然连着过去,仍然感恩,仍然传承着那些赋予我们姓名与故事的人。
哪怕你是在福建的樟树下为祖坟除草,或是在新泽西的出租房里上网查如何折纸元宝,你做的事,其实和祖先们一样:向后看,向前行,血脉不息。
一首清明诗
一首清明诗
跨越王朝,漂洋过海,最能道出清明节神韵的,莫过于唐代大诗人杜牧(803–852年)这首传世之作: Dynasty 唐朝:
清明時節雨紛紛,
路上行人欲斷魂。
借問酒家何處有?
牧童遙指杏花村。
路上行人欲斷魂。
借問酒家何處有?
牧童遙指杏花村。
A drizzling rain falls on Qīngmíng Day,
The mourner’s heart is breaking on the way.
I ask where can a tavern be found?
A shepherd boy points to Apricot Blossom Town.
The mourner’s heart is breaking on the way.
I ask where can a tavern be found?
A shepherd boy points to Apricot Blossom Town.
这里,悲伤与生者同行。雨水不仅是天象,更是记忆的承载。旅人愁思满怀,寻觅片刻慰藉。雾中,牧童一指,指向的是温暖,是歇息,是希望。
这,正是清明的核心:缅怀悲伤,却不困于悲伤;承载先人的故事与精神,不是当作负担,而是方向。
静静思念
无论你的祖先长眠于梅县乡间,雅加达郊外的荒地,还是古巴的无名土丘,你的记得,依然重要。你翻出一个名字,保存一个故事,修复一张照片,都是这场跨越千年的仪式的一部分。
你并不孤单,你走的这条路,千万人也曾走过。哪怕我们已无法跪拜旧碑,仍可心怀敬意,低头一鞠。
这个清明节,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向山靠近一步——哪怕只是靠近它的回忆。
愿祖先的声音,在我们心中响得更清晰一些。
想阅读更多華人祖先研究群 (Chinese Ancestry Research) 的文章, 请扫描任一图片右下角的二维码,点击链接后按“加入”。
一首诗,献给清明的静思与深意。
查看文章的 原始